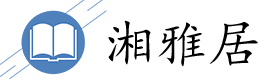宋紅娟 | 爺和婆
原標題:宋紅娟 | 爺和婆
爺和婆已離開我們整整22年了,他們兩人是同一年先後離世的:爺81,正月走的,婆75,六月走的,傳說中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悽美愛情也不過如此,我的爺和婆是現實生活中讓我感動的伉儷情深,一個走在了前面,不管是先走了的那個人放心不下那個未走的,還是那個未走的牽掛那個已經走了的,他們同一年先後離去,便是不離不棄。直到現在,自己也已經結婚生子,我更是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時時想起爺和婆的一世情緣——生活平淡,同甘共苦,不離不棄。
其實我的爺和婆,是我的姥爺和姥姥,說起這,還真有很多事得說一說。
爺和婆一共育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。兩個女兒是親生的,兒子是抱養的,排行老二,我叫伯(bei)。在爺和婆那個年代,生兩個女兒會被人瞧不起的,不孝有三,無後爲大嗎!聽說這期間婆也生過一個兒子,可是不幸夭折了,不知是傷心,還是身體的原因,婆有好幾年一直沒有再生個一男半女,於是就有了換個兒子的想法,這法子在當時很普遍,生女兒多的白送人,多生了兒子養活不容易,但要送人還要講講條件,看是給錢給物,因爲男孩長大了可以充勞力,掙工分。於是,在那個兒子是稀缺資源的年代,爺和婆想到了一個延續香火的法子:換兒——爺用一頭牛給我換回來一個伯(bei)。
待到兒女都到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年齡,難題又來了,嫁女容易娶媳婦難啊!於是,我能幹的爺和婆,又有了不讓伯打光棍的辦法:換親——大姨嫁給了姨父,姨父的妹妹則成了我伯(bei)的妻子,男不送彩禮,女不陪嫁妝,可以說女有嫁,兒有媳,皆大歡喜。不過,我後來聽說,厚道的爺和婆,因爲想着是姨父家是靠近縣城的(現在的鐵豐村,算城中村),女兒是高攀了,姨父的妹妹是下嫁了,所以爺和婆在大姨出嫁的時候,多送了兩口袋的麥子。
下面再說說我母親。爺和婆換回伯以後4年婆生了我母親,也許是爺和婆內心裡總有那麼一些擔心,畢竟伯不是親生的,所以到了母親出嫁的年齡了,能幹的爺和婆又有了私心:給母親招個上門女婿,於是,在那個信息不發達的年代,也不知爺和婆用了什麼法子,找了多少媒婆,終於給母親找了一個合適的人選,我的父親從此走進了爺和婆的生活,而且還是個掙工資喫商品糧的工人,這在當時可是不得了,不知要羨慕死多少人了!爺和婆再也不擔心自己老了以後沒人管了,而且他們還能有白糖、白面喫,這是父親當時工廠的福利。說到這,又得插幾句,這也是我懂事之後一直疑惑的問題:父親是怎麼被爺和婆看中的。後來我知道了,原來父親的老家在湖南,家裡兄弟姊妹6個,父親排行老四,家裡生活很困難,好在後來父親當了兵,喫穿國家管,再後來,父親轉業到了寶雞,這就離老家太遠,婚姻大事家裡沒法管,也管不了,娶個媳婦太難了,於是爺和婆託村裏一個在寶雞工作的大叔給母親找婆家,這樣,父親各方面的條件在當時都符合上門女婿的條件:離家遠,自己的父母操不上心;在寶雞當地,自己也沒有什麼親戚朋友;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父母身邊,也不用太操心父母的養老;自己的工作在寶雞,家必須安在寶雞當地;母親年輕時也確實長得俊,人也勤勞能幹。於是,憨厚的父親雖然是喫商品糧的,但他還是沒有太過挑剔,就帶着他的一顆赤誠之心開始了他往返寶雞和鳳翔的生活,盡心爲爺和婆養老送終,這在我們村成了一段佳話。
這樣,我的姥爺和姥姥,我和哥哥妹妹就一直叫做爺和婆,舅和妗子就叫做伯(bei)和大大(dada)。以致於我姨家的孩子又把我父親叫做舅,把我母親又叫做姨。怎麼樣,這關係是不是有點亂啊,確實,我曾經都有一段時間搞不清楚,不過,這正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生活折射。說這些,我還是爲了要說爺和婆,這樣兩個很普通平凡的人,卻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裡,把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周旋得很是得體,兒女們的生活都越來越好,爺和婆也總算是過上了人人羨慕的含飴弄孫、安享天倫的晚年生活了。
說起爺和婆,這話就說不完,停不下。
小時候,由於父親要上班,母親要勞動,所以我們兄弟姊妹四個大多時候是由爺和婆帶大的。我的印象特別深刻,小學上學第一天,是爺拖着我的手,親手把我交到老師的手裡,我記得還是爺給我交的七毛錢的學費;我背着的是婆給我用各種碎布頭縫製的布書包,這個在當時看着不怎麼起眼的書包,現在可以說是難得的工藝品。只可惜當時沒有手機照相機,沒有給這件工藝品留下一張照片,真是遺憾。
再長大一點,我每天除了上學,就是和同村其他的孩子一樣,幫着家裡大人幹活:挖豬草挖薺菜,拾幹樹葉當柴燒,女孩子還要洗衣服,折麥稈,編草辮,現在的孩子沒有了這樣的活計,當然也就少了很多的樂趣。如果說這些樂趣是我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,那麼比起爺給我講的故事來,它們可就要退居其次了。直到現在,我所對於文學的愛好,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受爺的影響。前面說了,我自小隨着爺和婆生活,所以每天幹完了所有活計,我最期待的就是晚上躺在爺的身邊,纏着他給我講故事。什么女媧補天,精衛填海,哪吒鬧海,沉香劈山救母等神話傳說;半夜雞叫,雞毛信等勞動人民與剝削階級的矛盾鬥爭;三娘教子,薛平貴徵西,穆桂英掛帥等歷史故事,爺的頭腦裏似裝着永遠都講不完的故事,正是這些故事,不僅鮮活了我童年暗淡的生活,而且豐富了我的文學積累,也激發了我的文學愛好,以致於使我每次的作文都優於別人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,從小學到高中,凡是舉行作文競賽,都有我參加,而且還能得個獎什麼的,我記得我初中三年的英語筆記,全是做在我作文競賽所得的皮面筆記本上,筆記本的扉頁上總會有一個大大的「獎」字,我曾經引以爲豪,這些筆記我一直保存着,甚至有一次還拿出來給兒子炫耀:「這是媽當年作文競賽的獎品,做的英語筆記你還能用!」直到後來在縣城買了房準備搬家,覺得這些東西太老舊了,就把它擱置在了農村的老家,不知道現在還能不能找得到。
現在,信息流通方便快捷,手機電腦有大量的電子書可讀,家裡的書櫃裡也有很多的書,可是我的頭腦裏總縈繞着的揮之不去的還是爺的故事:「和風細雨下在平川平地,惡風惡雨下在窮山惡水」;「只見那孫猴子站在雲端,手搭涼棚,用那火眼金睛定睛一看」;……這樣的語言風格不僅讓人印象深刻好記,而且它於寫作閱讀也有很大的幫助,爺是我的驕傲。
爺還有喜歡喫芝麻醬的愛好,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,一瓶芝麻醬可是奢侈品。爺買芝麻醬的錢可是他辛苦種菜、挖藥賺來的。我們家的老院子後面有一塊地,爺就在裡面種上黃瓜、西紅柿等時令菜,待到成熟季節,他就摘好菜,捋碼(收拾)整齊,然後提個籃子,帶到公社門口去賣,換一兩個零花錢;有時他會去崖(舊讀ai)邊挖一種草藥,然後曬乾了去賣。雖然當時家裡的開銷有父親的工資,可是家裡人口大小8個人,花錢的路數很多,爺說自己能動彈,賣一兩個零花錢自己用起來方便。所以,當爺屋子那個掉了漆皮的木柜子發出櫃門開合的吱扭聲的時候,那一定是爺新買了一瓶芝麻醬,然後爺就會在喫飯的時候,在軟軟的酵面饃饃上面抹上一層芝麻醬,讓這個黑面饃饃立馬就有了不一樣的味道。我也學着爺的喫法嘗試了一下,真的是香啊,喫完嘴裡還留有餘香,這是我兒時記憶裏所喫過的最香的東西了。現在,自己上班掙錢了,我在各大超市找尋着芝麻醬,也買回來喫,可是卻找不到了兒時爺買的芝麻醬的味道,我甚至想是製作工藝不對,還是原材料有問題,所以至此,我再也沒有了買芝麻醬喫的衝動了。
我記憶中婆是一個特愛乾淨的人,她最喜歡穿的是用白色的確良布(七八十年代的一種布料)做的斜襟布衫:夏天一件當外衣,秋冬一件當襯衣,我好像從來沒有發現婆的白色的確良衫子髒過,它時常被婆洗得白白淨淨的;婆那個年代,婦女要裹腳的,因而婆也纏足裹腳,每每看到婆洗腳的時候,一層一層取下纏腳布,我就感覺好像是在剝一層死皮一樣的痛,可是婆已經習慣了,而且絲毫不會因爲纏了腳就影響她幹活的利索:擀麵、蒸饃、燒火、燒炕、割草、餵豬,一樣都不落後;那時候,家裡人口多,錢來的不容易,所以我們姊妹四個的衣帽鞋襪基本都是婆一針一線做出來的,我最喜歡看婆擰麻繩納鞋底,婆納的鞋底花樣多,緊密結實,在當時那個農民在地裏刨食的年代,一雙結實的布鞋可是會讓做工的家人穿着腳更舒服,少磨點泡。在她的影響下,我的母親也是個做活的行家裡手,家裡頭的裏裏外外,被我能幹的婆打理得是井井有條。
爺和婆一輩子,沒有遠離過自己的家,但他們將近60年風裡雨裏走來,始終同甘共苦,不離不棄,脣齒相依。當然,就像牙齒偶爾還會咬了舌頭一樣,他們也有拌嘴的時候,但我的記憶裏,總是爺讓着婆,這個時候,我總是會發現婆眼睛斜瞅着爺但卻滿臉是笑,再來一句「死老頭!」爺這個時候也總是會笑着回懟一句:「把我罵噶你就高了!」然後兩個人又跟沒事人一樣,各忙各的。
爺不像其他老人一樣,閒了愛出去溜達,或者坐一塊嘮家常,掀花花(一種紙牌),爺沒事的時候,總會圍着婆轉:熬點功夫茶給婆喝;婆編草辮的時候爺也會學着編;婆要燒炕了他就去拾掇柴;可以說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,婦唱夫隨。也許有人會說,爺作爲男人沒出息,成天圍着老婆轉。可是我要說,這也許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:平平淡淡但卻實實在在,大有你若安好便是晴天,你若幸福便是終點,你若不離我亦不棄的味道,真是羨煞旁人。
爺和婆的故事似乎一說起來就沒有個完。每每在夜深人靜,我的腦海裏就會冒出來爺和婆這兩個字眼,也每每會讓我淚打枕巾,好想念他們。但我想,他們一定會在那個世界裡,相互攙扶,一起看大戲,逛廟會;也會一起坐在飄滿花草香的院落裏,看那星星和月亮。
宋紅娟,鳳翔縣彪角鎮中學語文教師,一個喜歡平平淡淡生活的人,偶爾用筆記錄下自己生活的點點滴滴,希望在時光的穿梭中能夠撿拾生活的真善美。
(公衆號轉載須聯繫授權)
主 編 | 風 行
主編
原創文章,作者:逐道長青,如若轉載,請注明出處:https://www.sxyt.net/119013/